贺绍俊:田苹长篇小说《花开如海》序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5-17 作者: 贺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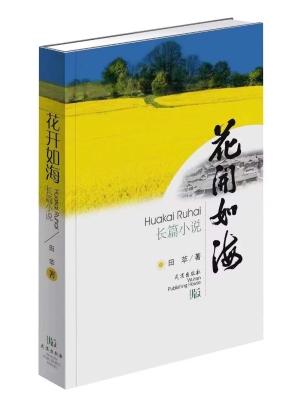
田苹的《花开如海》讲述的是在扶贫工作中发生的故事。
几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展开的脱贫攻坚战我们还记忆犹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终于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脱贫攻坚战中,文学始终没有落伍。许多作家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他们对扶贫工作充满热情,也从扶贫工作中吸收到丰富的创作资源,近些年,不少反映扶贫工作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给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道崭新的风景线。田苹的《花开如海》便是这道风景线上一个格外耀眼的景点。
《花开如海》的耀眼之处首先是它的真实感和现实性。《花开如海》是完全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小说。在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的关键阶段,田苹所在地区创新扶贫工作队派驻模式,他们在全州组成了两千多个脱贫攻坚“尖刀班”,奔赴一线,以村为战场,户为堡垒,集中精力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落实。《花开如海》写的就是其中一个派驻到春树坪村的尖刀班的故事。我没有询问田苹本人是否也曾参加过尖刀班,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有不少就是尖刀班的成员,她一定听到不少关于尖刀班所发生的故事,她也一定为写这部小说进行了认真的采访调查。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显得活灵活现,仿佛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走出来似的。田苹充分施展了她讲故事的叙述能力,虽然写的是扶贫工作,但她没有把自己的视野拘禁在扶贫工作上,而是将扶贫工作与尖刀班成员的家庭和日常情感融合在一起来写,尖刀班的四名成员是从各个部门抽调上来的,既有经验丰富的转业军人,也有刚刚考入公务员的年轻小伙,还有在家里被母亲当成小公主对待的姑娘,甚至还有一位是不满于在家无忧无虑生活、要出来见见世面的“拆二代”的临时招聘司机。他们抱着不同的心思参加尖刀班的扶贫工作,但面对乡村的现实,以及与贫困户的相知相熟悉过程,使得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尖刀班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仅完成了脱贫任务,而且还使每一名成员在思想境界和人生经验上收益良多。
《花开如海》的耀眼之处还缘于作者在写作中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理念出发。一般来说,反映扶贫工作的小说是一种主题性写作,在主题上基本上有明确的要求。有些作家写这类题材的小说很容易陷入主题和概念之中,人物和故事都是围绕主题和概念走,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小说,主题倒是很明确了,但人物都变成了一个个符号,故事也显得很虚假。田苹的可贵之处是从生活出发,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田苹善于从生活中发现那些似乎与主题和概念不太一致的内容,她愿意在这些内容上做文章,这不仅避免了创作上的同质化和模式化,而且也是在考验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因为这些看似与主题和概念不太一致的内容只是表面上显得不一致,它应该只是主题和概念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所作的调整,从本质上说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作家只有从思想认识上把握住了这一点,就能找到表面上的不一致与本质上的一致这二者之间的通道。比如小说特别强调了乡村农民对扶贫工作的意见和不满,但作者认识到这是扶贫工作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尖刀班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解决好大家的意见和不满,真正让扶贫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农民的心中。因此小说不仅不回避农民的意见和不满,而且还要将其作为尖刀班开展工作的重要环节来写。小说写到漆班长决定不按惯常的做法开村民大会,而是要让尖刀班分别到各个屋场去开屋场会,因为村民大会一般是各级领导讲话,然后村民表态,听不到村民们真实的声音,只有下到屋场,村民们才会无所顾忌地说出他们的意见和不满。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尖刀班了解到大家的想法,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消除了村民们的疑义。又如小说还写到了村民的迁移。我在不少反映扶贫的小说中都读到迁移的情节,因为迁移也是脱贫的措施之一,但我发现,大多数小说的迁移情节写得都不是非常理想,因为作家们往往是从概念出发来设计情节的,他们觉得既然迁移是扶贫的需要,在情节安排上就一定要让不愿意迁移的村民最后都迁移了才对。田苹从生活中发现迁移工作同样是复杂的,会面临各种情况,以一个统一不变的规定是难以解决情况的复杂性的。春树坪中就遇到了杨凤玲和幺婆婆这两类不愿迁移的难题,尖刀班的同志们不是生硬地要求他们一定要迁移,而是理解他们的难处,并从他们的特殊情况出发,拟定出分散迁移的方案,他们这样做才是真正从人民利益出发,想人民之所想,因此也得到县政府的支持,最终也使杨凤玲和幺婆婆都有了各自圆满幸福的结局。
《花开如海》的耀眼之处更与作者田苹对主题的深入开掘大有关系。主题性写作往往容易流于主题的一般化宣传上,比如关于扶贫主题,作家们会在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伟大意义上做文章,会在塑造扶贫英模形象上下功夫。当然,这方面的主题在《花开如海》中也有所体现,但作者在此基础上又对主题作了多方面的开掘。其一,小说还从党群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尖刀班的意义。尖刀班是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一种有效措施,就像小说中所写的尖刀班下到春树坪村后,各项扶贫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但尖刀班的作用不止在工作层面,而且还代表着党的形象,他们就像一根纽带密切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漆班长便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他对尖刀班的成员们说:“在老百姓眼里我们就是党就是政府就是国家,我们做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走东家去西家,他们都看在眼里,既是监督更是希望!”小说就写到了这样一个自觉代表党和国家的尖刀班,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是从每一个细节做起的,他们也主动与村民们建立起亲切友好的关系。其二,小说还以大量笔墨讲述了尖刀班成员们的成长和磨练。当叶副县长看到田子嫣和彭晓阳这两位年轻人的巨大进步后特别欣慰,他感慨地对两位年轻人说:“与其说是你们在扶贫,不如说是乡村社会在对你们进行扶贫。”叶副县长的意思是说,两个年轻人经历了几年扶贫工作的锻炼,他们曾经在精神上的贫乏得到了克服,他们的思想也变得更充实了。事实的确如此,在脱贫攻坚战中,大批的干部抽调到扶贫工作的队伍中,到乡村去,到贫困的农民中间去,他们在开展扶贫工作的同时,也在接受乡村的思想洗礼。田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小说中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出来,从而增加了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亮点。
田苹始终是以一种积极、阳光的心态写这部小说的,这无疑也是《花开如海》耀眼的重要原因。小说写到了乡村的落后与艰难,写到了人心的龌龊,写到了死亡和挫折,但这一切并没有变成阴霾遮蔽住田苹的眼睛,压抑了田苹的呼吸,因为她的心头始终被阳光照射,她能感受到时代的希望,她怀着希望去面对现实,这就使得她的叙述不会是沉重的,也不会是灰暗的,更不会是绝望的。她的叙述是明快的,也洋溢着一种生活的热情,传递出积极、阳光的心态。这种积极、阳光心态下的叙述恰好应和着时代的主旋律。
尽管从小说艺术的整体性与完美度来说,我们可以指出小说这样那样的一些毛病和不足,但即使如此,我也要说,《花开如海》为我们的主旋律文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文本。




